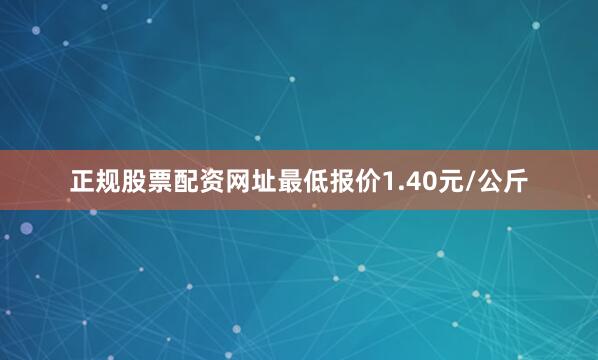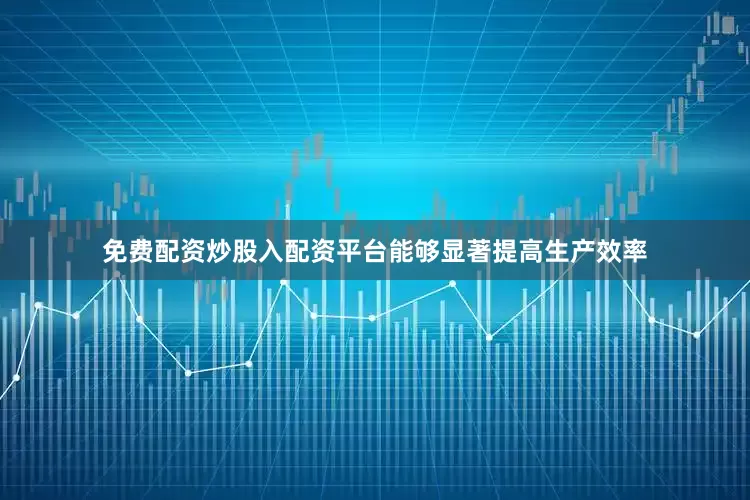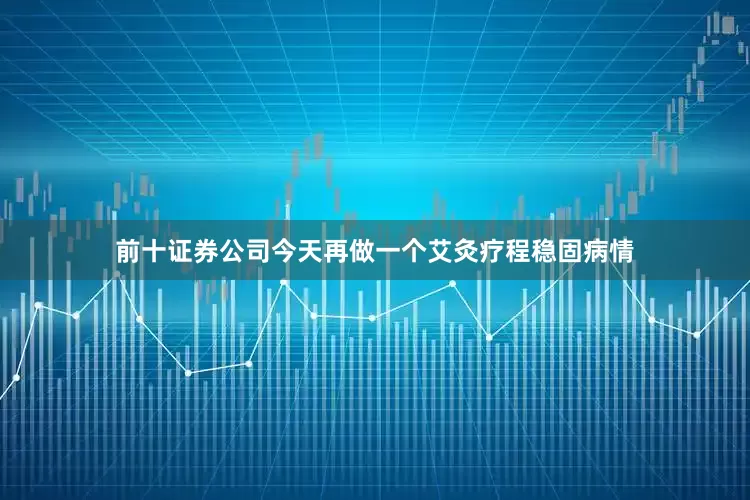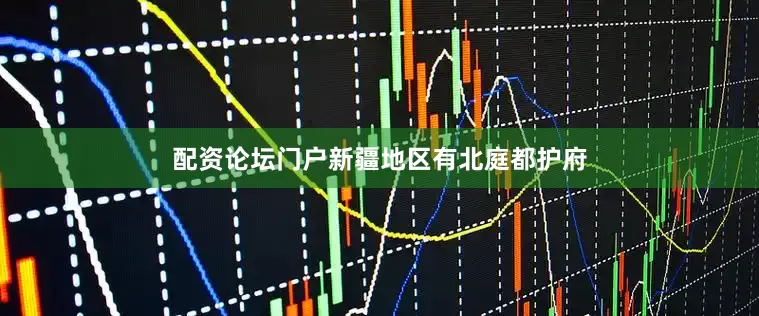

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,元朝的标签很简单:“蒙古入侵”、“外族统治”。
历史课本上三两页就翻完了,影视剧里镜头也总爱对准元朝将领战马、长刀、杀戮的场景。元朝看起来像是一段中国历史上一段阴冷的插曲。
可你真把历史典籍翻开,仔细查阅,你定会意识到,元朝历史并不是这么单薄的。

元朝的存在,不只是草原骑兵踏破城门那么粗暴。它在版图、制度、经济、文化上,给中国动过一次“大刀”,直接把中国历史的走向改了个方向。
更值得一说的是,元朝还在无形中给中国堵住了一条路,那条可能让中国走向欧洲中世纪式长期割据、宗教与政权混战不休的路。
大家可以试着想象一下,如果没有元朝,南宋、金、西夏、大理这些政权各守一隅,互不统属,南北像隔着一道厚墙,边疆慢慢脱落,文化认同会在地理的缝隙里分化。那不是危言耸听,欧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,几百年都没能合拢。
元朝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?元朝到底做了什么,防止了中国滑向“欧洲化”的那条岔路呢?
一、统一与版图塑造:从“小中国”到“大中国”
在安史之乱之后,中国的版图变为了七零八落的碎片,近四百年时间都没凑完整。
辽、金、西夏轮番在北方坐镇,南边是北宋、南宋缩在江南的半壁江山。西南的大理自成王朝,青藏高原上吐蕃的旧势力分崩离析,各地政权像一锅煮开了的水。

谁也压不住谁。南宋人自己都叹气:“大渡河外非吾有也。”
那种对西南和高原的“无意为之”,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。

蒙古的崛起打破了这种沉闷的格局。1206年,成吉思汗在草原上集结诸部,那一刻的风声和马蹄声,从戈壁吹到大漠,再到黄河边。

半个多世纪之后,1279年,忽必烈灭掉南宋的最后一支舰队,崖山海面上漂着无数残旗。历史上的“大中国”从此落地。中原、草原、西域、吐蕃、云南,像被一双粗糙的手用力按在一张桌子上,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地图。

疆域,2200万平方公里。北至西伯利亚,南到南海,西到咸海,东到朝鲜半岛。这不是纸上画出来的空线条,而是真有人在巡边,有驿道、有军屯、有赋税。和汉唐那种转瞬即逝的“大帝国”不同,元朝的统一是有黏性的。

北京大学的张帆教授说:这是“大中国时代”的开始。
意思是,从元朝之后,广域的统一变成常态,而不是偶尔的运气好。
看看云南,唐宋几乎没碰过,元朝直接设行中书省,还安排土官与汉官双轨并行,把山里的部族编进册子;西藏则设宣政院,政教合一,中央直接派人管。
这些地方第一次听到的,不是盟誓的口号,而是来自大都的诏令。
忽必烈把自己放在一个全域之上的位置,他的地图里不再有所谓“非吾有”的灰色地带了。
二、制度与行政网络:省制、驿站与边疆治理
元朝统一只是个开始,地图画好了,这不等于你能管得了那么大的地盘。
元朝面对的,是一个比汉唐还要辽阔的版图,里面塞满了风格各异的民族、语言、宗教。
忽必烈和他的幕僚必须回答一个现实的问题:怎么让这些地方听你的,而不是看着地图点点头、转过身各过各的日子。
他们想出的办法,就是那套后来被明清照搬的“行省制度”。
中央有中书省,下面分十多个行中书省,一级一级直通皇帝。别小看这套架子,在辽、金、宋的时代,从中枢到边陲,信息传递和行政调度都像隔着厚厚的棉被,而元朝的行省,把地方直接拴在了中央的腰带上。

边疆的手笔更大。岭北、甘肃、云南、辽阳这些地方,元朝直接单列成省,不是虚衔,而是真派官去管。
西藏由宣政院直辖,下面分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,既管宗教,也收税、屯兵。
新疆地区有北庭都护府,南海之上,1350年还特意在台湾设了澎湖巡检司,这是中央第一次伸手到台湾的官方动作。
换成以前的王朝,很多地方能管到河北、两湖就算极限了,西南、西北、海外只能靠羁縻和封号安慰。
当然,光画格子不够,格子之间得有线连起来。元朝在全国布下了密密的驿站。
史书记着,全国有站赤1380多处,还配急递铺,快马加鞭,从大都发出的军令,可以在最短时间里送到西藏高原、送到漠北草原。

大家想想在那个没有电话、没有铁路的年代,这是一条条用马蹄和尘土踩出来的血脉。
还有粮食的事。北方人口多,地不够肥,元朝就动了南粮北运的脑筋。他们开凿了济州河、会通河、通惠河,把江南的稻米从杭州、温州、明州这些港口装船,沿海北上,直送到大都。
年运粮三百万石,不是零星的买卖,而是国家层面的粮食动脉。沿途还有转运站、仓库,海上的粮船就像今天高速公路上的货车,一艘接一艘,把南方的温润和肥沃送进北方人的饭碗。
这套制度和网络,让元朝第一次真正做到了:地图上画的,不只是边界线,而是能伸手触到的疆土。

三、经济与全球化:海陆丝路的复兴
元朝统一之后,最大的变化之一,就是南北经济被强行接上了管道。
之前几个世纪,南北之间有贸易,但路线不稳,沿途政权林立,税卡林立。
统一之后,南方的稻米、丝绸、茶叶,可以有计划、有规模地输送到北方,北方的马匹、皮货、金属也能稳定送到南方。这种双向流通的前提,就是政权对全域的控制力。
陆上丝绸之路,在蒙古的军事保护下恢复运行。
从大都出发,西行经河西走廊、天山南北路,可以直接到撒马尔罕、巴格达,再延伸到地中海的港口。安全性提高,商旅和货物的规模也随之扩大。
海上丝绸之路同样进入高峰期,泉州、广州、温州、杭州、上海等主要港口,都设立市舶司,由国家统一管理进出口和征税。
泉州港在元代的地位尤其突出,不只是中国的第一大港,也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贸易港之一。

来自中原和江南的瓷器、丝绸、茶叶、铜器,经此地运往日本、高丽、东南亚各国,甚至远达波斯湾和东非。
史料记载,1293年,伊利汗国派使者来大都请求引入中国的纸币制度。元廷派专员赴波斯建立钞库,中国纸币由此正式进入西亚。这是纸币在世界流通史上的一次重要跨区域传播。

国内的商业环境,也因统一而改变。大都、杭州、泉州成为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商贸中心。
元朝在税制上对江南相对宽松,一亩田年税三升,农民负担减轻,手中有余力参与市场交易。棉花种植在这一时期迅速普及,黄道婆从海南带回的先进纺织工具,使棉布逐渐取代麻布,改善了百姓的衣着条件。

景德镇的瓷业生产,在这一时期形成规模,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,还大量出口。
可以这样说,元代的商业组织中,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资本积累现象。大型商号、工坊的运作模式,使资金、劳动力和市场形成稳定循环。
四、防止“欧洲化”的历史意义
以上说了这么多。
各位可以设想一下,如果元朝没有完成统一,中国的格局会是什么样?
很可能是南宋、金、西夏、大理等几个政权长期并存,各守一隅。
南宋的疆域只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左右,金朝也不过三百六十万。南北政治、经济体系不同,文化认同逐渐分化。
时间一长,南方汉人和北方汉人未必还会把彼此视作同一民族,边疆的契丹、吐蕃、回鹘等族群也可能走向独立。
欧洲的中世纪史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例子。
查理曼帝国解体后,西欧被切成无数小国,疆界频繁变化,王朝战争、宗教冲突此起彼伏。法、德、意这些后来各自成国的民族,最初在文化和语言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,但分裂和战争把他们彻底隔开。

统一直到近代才在部分地区实现,而且代价极高。
元朝的出现,把这种可能性提前掐断。它不仅在军事上击碎了所有割据政权,还用行省制度、统一的税制、全国性的交通和贸易网络,把不同区域、不同民族硬性捆在一套政治结构里。
这种整合,使南北互通变成常态,让边疆事务纳入中央直接管辖。
雍正曾说过一句话:“塞外之一统始于元。”

这不是一句泛泛的称赞,而是实情。元朝完成的,是版图上的一统,也是制度、经济、文化上的全面捏合。从那以后,“中国”不再是几个地区的松散称呼,而是一个固定的政治与地理概念。
多民族共存的框架,从理念变成了现实,并且延续到明清数百年。
结语
最后,笔者再来总结一下!
元朝的历史并不完美,它有民族等级、财政困局等问题。但它在统一版图、完善行政、打通海陆丝路、推动经济全球化、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成就,是任何前代都难以企及的。如果没有元朝,中国很可能陷入漫长的割据和内耗,失去成为统一大国的历史机遇。
可以这样说。
在大历史的尺度上,元朝不仅塑造了今天中国的地理与民族格局,也让“大一统”成为此后中国政治的常态。这正是它留给后世最深远的遗产。
参考资料:
1、访谈︱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:元朝开启了“大中国”时代 来源:澎湃新闻
2、《对《元史》本纪史源之探讨》 王慎荣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
3、《国家大一统 民族大团结是民富国强的重要条件-读元史之我见》刘益华
4、《我怎样研究元史》 方龄贵



本地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炒股怎么加杠杆有以生命为盾守护百姓的脊梁
- 下一篇:没有了